文苑|回忆恩师杨清如先生
由于杨清如所处时代,有关她生平的文字资料并不多。现在网络上有关她的报道,都是一些见诸报刊杂志的文章转载,而这些文章的撰写者大都没有见过杨清如,不过是源自两个出处。一是段云璞的报道,一是唐中六的《巴蜀琴艺考略》。当年段云璞对杨清如的报道,虽然来自杨清如口述,真实性不容置疑,但只是从介绍重庆古琴的角度进行的简略报道。唐中六一直在成都,来重庆与杨清如相见交流毕竟也很有限。我虽然自1988年向恩师学习,直到她1995年弥留之际都独自陪伴,但那时的我尚年轻,很多重要的史学,甚至琴学本身的渊源,都不太懂得如何去珍惜,更谈不上会留心去向恩师系统性请教和记录有关她的生平事迹。而且,即便有些记忆,也缺乏资料证据,难以成为令人信服的史料。
正因为此,我常想,以现有这些文字资料,真的可以给杨清如先生写一个完整的生平吗?那么,我只想对恩师作一些回忆。这些回忆,虽然难以达到学术研究那样严谨上档次,但我觉得于斯世恰恰会有它富于价值的一面。因为能够让人回忆的,多是让心灵有过触动并在记忆深处刻下痕迹的东西。
写回忆,自然就省了好些文史必须的求证。比如有关天风琴社的由来,现在有很多种说法。按杨升平的说法:“我们祖上开的钱庄叫‘天顺祥’,我们杨家老院大朝门的牌匾上刻着“清白家风”,爷爷取两个的头尾,合起来,就是‘天风’”。还有专家从天风本身的词义进行考证,归结于当时琴人结社时比较共同的想法。这些都说得通,又都缺乏必要的证据。就我从恩师那里听来的,是她家书斋之名,在成立之前家人早就把书斋用作弹琴之处,就称之为天风琴馆。后来重庆成为陪都,名流汇集,大家想成立一个琴社,因为得到杨家的经济支撑,于是就直接在杨家这个天风琴馆基础上扩大规模。而天风的名字,本身就不错,自然也就沿用下来。记得我跟恩师学琴不久,恩师就给我讲到天风琴社,我主动问起天风的由来,恩师就这样告诉我。当时说者听者都很自然,但是现在这样说,就缺乏旁证了。还好,我这是在写回忆,讲自己的故事,回忆而已,权当野史罢了。不过,认真想一想,恩师的话不无道理。左琴右书,历来琴家将自己的书斋作为琴舍者不在少数。再看天风琴社那张照片,二十几位人物中,竟有杨少五几位家人。你可以想象,天风琴社设馆在杨家,琴馆的物质资助大部分来自杨家,沿用杨家原有的琴馆名,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谁会站出来说,这个新成立的琴社不要用杨家原来的名字,改成天风琴社更好呢?
我在1984年聆听古琴被感染后,学习古琴就一直成为我的梦想。为此我通过函授班学习了基本乐理,为日后学琴作了积极的准备。1980年代的中国,几乎就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古琴。1987年年初,父亲得知单位里有位同事的儿子在北京从事音乐工作,便通过他联系上北京乐器厂,预订了一张琴。价格是四百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收入者大半年的工资。据说北京乐器厂这时只有一位老师傅还能够斫琴,等了近一年,1988年春节前这位同事的儿子回重庆,将琴带回来了。拿到这张琴时,我是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古琴。好笑的是琴弦都张反了。这个时期产的琴弦,缠绕雁足的一端钢丝是露出来的,呈一个封闭的环形,乐器厂居然不结蝇头,直接将绒扣穿在这个环里置于岳山之上。而且,做琴之人似乎不懂捻动琴轸来松紧琴弦,而是在两个雁足中间另外绑上一块长方形木块,木块的两边拧上螺钉,琴弦的另一端就缠绕在螺钉上,像琵琶二胡那样来张紧琴弦。我这时也不懂,后来学习以后才明白。
接下来,就是找老师了。父母又托人去各个高校打听,可打听来打听去也没找到老师。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有些心急了,便在电话黄页上查找到重庆音乐家协会。八月的一天,我约上一位中学同学陪我一起到了音协,这时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间了。音协是个清冷的单位,没有几个工作人员,我们正好碰上音协主席叶语老师。虽然是重庆名人,但这个时代的文化名人完全没有名流的架子,当他听说我来找古琴老师,露出一脸的惊奇,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小伙子,你怎么喜欢这个乐器?”我对他简单述说了自己喜欢古琴的原由,他沉吟道:“古琴很高雅,但难听、难懂、难学!”他说这三难时话语一字一顿,给我印象很深。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说法,我从一开始在磁带上听到琴声而产生对古琴的浓厚兴趣,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才逐渐听出琴曲中一些细腻的韵味。同时,我逐渐感受到周围人们对古琴的反应,要向他们讲解琴的意趣,真是“难、难、难”!
过了几天,我的同学又陪我一起,按照叶老师给我的地址,在渝中区人和街找到杨清如的住所。这是一栋1960年代非常普遍的三层红砖楼房,底层的大门开在两端,大门处有楼梯,通往二三层。每层楼都是直通的过道横贯中间,房间分布两边,公用厨房和盥洗间则一般都设置在过道的中部。清如老师的家在底层,从右边大门进来的第一间。我们是吃过晚饭后来的,此时天色已暗,房门开着,门口挂着一张薄薄的布帘,透出很微弱的灯光。我撩起布帘,看到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屋顶中央垂吊着一只10瓦左右的小白炽灯,光线显得特别暗弱。依稀可以看到屋里的陈设,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各种东西密集地堆放着,显得拥挤凌乱。唯有屋子正中的一张琴桌,上面除了一张琴外什么都没有放,在室内其他物品的陪衬下显得特别清爽干净。我一直保留着一张1990年清如老师在这屋里弹琴的照片,照片的背景可以看到如许光景。此时我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坐在床沿上,她背对着房门,低头在整理着什么东西。我向恩师说明来意,她把叶语抄写地址的那张纸条凑在眼前仔细看过,对我点点头,这样我便开始了我的学琴历程。
老实说,初见恩师以及后来与她相处的相当一段日子里,除了满足了我长期学琴的愿望之外,我并没有在恩师这里获得我所希望找到的那种文人雅士飘逸超脱的风雅,甚至有些方面还让我颇难接受。
首先是古琴的音量和音色问题。我欣赏古琴是从听磁带录音开始的,之前我能听到的就是李祥霆、俞伯孙等几位琴家所录制的几首曲子,因为录音棚里录下的音,古琴的走音都可以听到。而在恩师这里,现场的琴声远不能与录音相比。恩师有一张宋琴,还有一张民国时期家里自制的纯阳琴,上下面板都是桐木。两张琴的音色都好,但都有些沙音,尤其是宋琴,雁足处明显不能承压,恩师为了维护这琴,把弦张得松些,这样琴的发声在正常音高以下,远没有我在磁带里听到的美妙。对于我这个年轻人来说,自然产生很多初学琴者容易生发的感受——古琴音量太小,进而会觉得古琴音色暗沉。我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都是主张古琴应该有更大音量的那种肤浅认识者。
还有就是恩师的生活习惯。学琴之前,我总是把弹琴之人设想为充满书卷气的优雅之士,家里也应该窗明几净,书画满堂,兰菊交映。而恩师家中摆设凌乱,屋子采光不好,堆的东西太多,散发出一些不清爽的气味。正应了这个时候一般人的普遍看法,就是传统的东西总是那么陈旧那么腐朽。这些似乎都延续着传统文化常常显现的那种荒冷而孤寂的表象。
尽管如此,我把恩师的生活习惯归结于年龄代沟。恩师那个年代的人,包括我的父母这些比恩师年龄稍小些的人,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掉,把个屋子堆得很满。而且看到恩师佝偻的腰背严重弯曲着,知道她毕竟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体状况,我也就理解她,努力去适应她的生活习惯。印象很深的一次,是1989年第一次参加恩师的生日宴,就在恩师家里。屋子正中的琴桌也是餐桌,中午,恩师邀请了她的姑妈和另外两位亲属,我这个年轻人和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恩师拿起生日蛋糕所配的塑料刀叉开始切蛋糕,这种刀叉不像钢刀那样锋利,结果恩师把蛋糕切得七零八乱,奶油弄得到处都是。恩师不时将刀叉上的奶油放到嘴里舔干净,又继续切。老人们接过恩师递过来的蛋糕,欢笑着,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恩师也把一块蛋糕放进我碗里,还特地用刀叉舀了一叉奶油给我,我用碗接过,极不情愿地一口一口慢慢吞下去。
到恩师家学习次数多了,对她慢慢有了更多的了解。
恩师家里有几个亲戚常来往。最初见到的是她的亲妹妹杨德如,时常与她一起生活。可惜恩师介绍时,让我称她二孃,所以这位妹妹的名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弄清楚。我还认识了恩师的一位姑妈,这位姑妈年纪很大了,和恩师的妹妹都属于那种非常清瘦的老人,身体单薄得好像一阵风就可以刮倒似的。姑妈要抽烟,穿着很讲究,听说喜欢打麻将。这些让我想起她们年轻时应该就是那种身着旗袍烫着时髦卷发,成天无所事事叼着烟坐在麻将桌上的民国美女。
亲属中来得较多的是一位张爷爷。我是在初冬见到他的,年龄比恩师略小。他抽传统的叶子烟,满身都是浓重的烟味。恩师让我称呼他为张爷爷,至于他叫什么名字,与恩师是怎样的亲属关系,我那时年轻,一直也没有再深究过。他的一只腿是瘸的,靠一只手扶支架来行走。张爷爷很健谈,从他那里我得知了很多关于恩师家族解放前的一些往事。特别是杨氏家族在当时重庆政商界的影响力,每每讲到这些内容,张爷爷显然有一种为杨氏家族当年荣盛颇感自豪之情。张爷爷还说起当年冯玉祥经常派警卫员来家中接恩师去他那里弹琴雅集。恩师在一旁点头,并说冯玉祥古筝弹得尚可。我还追问冯玉祥会不会弹古琴,恩师摇头说不会。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古琴对恩师的一些认识也在发生巨变。尤其是我发现传统文化带给我的孤寂其实在恩师这里早就存在了,于是我在恩师这里真正找到了这些年来苦苦追寻的高山流水的情怀。
我是从学习《关山月》开始的,之后又学了《阳关三叠》《酒狂》《醉渔唱晚》等曲,恩师在表现弹琴的轻重缓急上,对很多音都讲究轻弹,讲究右手手指肉甲的并用。尤其是听恩师弦歌,很多之前感知不到的韵味逐渐呈现出来。这让我逐渐体会到古琴传统的“韵多声少”,古琴的韵味很多是那种发声小甚至不发声的弦外之音营造出来的,只有长期的习练才能深刻体会到。这样,我彻底抛弃了之前听恩师现场弹琴总觉得古琴音量小音色暗沉的那种感觉。
1991年是我学琴的第四个年头,这时我已经能弹《梅花三弄》《渔樵问答》等大曲,于是我主动向恩师提出要学《潇湘水云》。从这个时候我才算真正认识恩师的琴学修养。
之前只知道恩师喜欢《渔樵问答》,经常弹唱给我听,而《潇湘水云》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主动弹过。跟她学习此曲,才知道此曲原来也是她最喜欢的曲目之一。恩师弹此曲,本《五知斋琴谱》和《琴镜》谱,又参合重庆同好手抄吴景略谱本,故而深得该曲神韵。而我喜欢此曲,始于1986年期间重庆电台播放的李祥霆领衔的古琴与乐队合奏曲,后来又听过龚一的独奏版。当我学习到曲子的中后段,记得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恩师家又学了一段,这一段名指从一弦开始,依次在各弦十二徽和徽外交替注绰,旋律激进上升。这段乐段是李祥霆和龚一录音中没有的,之前恩师弹到这里我也注意到了,现在学完这段,有了自己的体会。当我再一次听恩师示范,旋律直入我心,引得心神激荡,不觉流于行表,在一旁直呼“太好啦!”恩师将手停下来,眼神从琴弦上抬起来侧看着我,嘴角泛起一丝轻微的笑意。在这一笑之中,我分明看到恩师眼中烁烁的目光,这道目光正好与我的眼神相撞在一起。我看到恩师眼光里对我的肯定,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肯定,我从恩师的眼神里还读到了我长期以来渴望的那种知音间的会心一笑。要知道,我之所以向恩师主动提出要学《潇湘水云》,是因为这首乐曲对我产生了特别深的触动。曾经多少次我爬上重庆郊外的山头,心中哼着《潇湘》的旋律,把峰顶踏遍,涕泪四流。我以为我能够体会到的古琴最深刻的思想情怀都在这首曲中。而现在,我和恩师的心神竟在这深刻之处不期而遇了。应该说恩师只是把我视为了一个难得的学生,但我此时却将恩师视为了知音。恩师这道目光向我诠释了会心的真正含义,这是我的生命中第一次感受这样的笑意,期盼了很久,而当它真正出现时,又大大超乎了我的预想。于是,这一瞬间刻骨铭心地凝结在我的记忆中,烙入心田,永生难忘!
从这之后,我之前对恩师那些因为年龄代沟所致的生活习惯差异的感觉骤减,我对她产生了家人般的感觉。每次去她那里学习,我都愿意留下来与她一起吃饭。我会买一些卤菜之类的下饭菜,而她也明显表现出对我慈母般的关怀。我发现,除了正餐之外,一般情况下还可以吃到银耳莲子汤、黑芝麻汤圆之类的自制保健品,以及各种点心水果。恩师虽然身体不好,弯腰驼背,但头发一直都是青丝,直至辞世都没有白发,这可能与她常常自制这些保健品有关。
在恩师家里呆的时间长了,发现房间的凌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空间造成的。因为缺少大衣柜和碗柜之类的家具,很多物品只能叠放在一起。但那些看似杂乱的锅碗瓢盆,里面盛着什么物品,恩师心里非常有数。我还看到之前忽略的很多细节,比如沙发,说是沙发,千万不要理解成那种高档的真皮或者布艺沙发,而是那个年代流行的一种自制的布料沙发,这种沙发往往不到一年时间,内部的弹簧就开始出问题,造成沙发表面凹凸不平。恩师在沙发上很少放置多余的东西,沙发后面的那面墙,虽然墙体斑驳,但清清爽爽。原来墙上有一幅画,后来恩师把我写的一幅书法立轴换上去。那是我专门写来送给她的,书法的内容是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开场的那首诗: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慢慢地,恩师对我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教完我所学的乐段,我开始练习时,她就在一旁削水果。握着恩师递来的水果,很多时候,我环顾这个狭小的房间,静静地看着墙上我写的那副书法,在心里默念着冯梦龙的诗。我觉得我同她,是师生,更是知音!
恩师妹妹辞世后,起初姑妈和张爷爷也经常来,或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后来也少来了。至于学生,就我所见,恩师前后收过七位。除我之外,都是女性。在我之前有两位,一位学了几个月就因为工作移居外地了,我们后来也曾谋面。另一位据说之前就有些古琴基础,我看到她时已经能熟练弹奏《关山月》,在跟恩师学《醉渔唱晚》了。这位师姐也算积极,但不知为何后来就来得少了,到后来偶尔来一次,先前弹的曲子也手生了。我之后的四位,其中一位也是因为工作移居外地,同恩师学琴时间较短。倒是她介绍的一位小姑娘小宋,虽然没学到什么曲子,但前后断断续续来恩师家超过两年。还有一位是在校的中学生,因为喜欢武打片,被其中古琴的片段激发一时兴起,听恩师说总共就来上了三次课,我一次也没碰上,只见过她写给恩师的一封信。
这个时期古琴是冷门中的冷门,求学的人本来就少得可怜,这几位学生能够主动找上门来学习,已经难能可贵了。当然,恒心或者说定力毕竟是更高一层的要求。一旦缺乏定力,会给自己造成一个尴尬的学习局面,尤其是这个时候,没有手机可以方便地录音录像,没有网络没有视频没有雅集,一旦在家不练,学到的旋律又得让老师从头教起。次数一多,且不说老师不开心,学生自己也会产生自责。再看到其他学生学得积极有效,便可能产生自卑,干脆就不再来了。
这样,从1992年开始,恩师基本上就是独自在家,我能感受到她的孤寂。恩师是那种话语很少的人,几乎不评价人。有那么两三次,我见过她表达对一个人的不认同,都是同样的表达方式,笑笑然后说“这个人多扯的。”重庆话“多扯的”有多层意思,诸如有点超出想象,有点滑稽,有点不可理解,等等。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句很温和的话。对于学生们缺乏定力,恩师便用这样的话向我表露过。恩师看重学生的定力,体现了她作为一个中华传统文人的基本素养。她既然能够向我表达对其他学生的这种看法,自然也是看到我能够持之以恒。多年以后我在唐中六先生那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唐先生当时是成都歌剧院院长,与恩师有交往。2009年我在广州参加一个琴会上遇见唐先生,他无意中说起恩师曾给他一封信中提到我。我后来专程去成都,在唐先生家里看到恩师这封信。这封信写于1993年9月,一共两页半,主要述说了她是如何保留那张宋琴,回绝了众多购琴者,其中不乏在她经济拮据时伸出援手的琴人挚友。信中提及到我,她说:“我的学生方文伟,学琴已五年,还有恒心,有认识,几年来对我生活非常关心照顾。”在恩师看来,我习琴五年对琴只是有一定认识,那么她显然更看好我的恒心和对她的感情。说实在的,恩师写这封信时,我那时二十几岁,与很多人一样,学了几年琴对自己颇为满意,因为肤浅,看不到前辈的长处,也就看不到自身的短处。现在手捧恩师这封信,既惊讶,也不惊讶。
小宋没有琴,我这时又在同学家借得一张民国时期的老琴,便把自己买的那张琴借给她。小宋学琴虽然远不及我积极,但她为人挺有人情味,每次来恩师家都要给老师买点东西。小宋过年过节都打电话给我,邀我一起到恩师家吃饭。恩师家里凌乱,小宋每次做饭时都顺做清洁,她做的饭菜也好吃。这样,1992年前后的各个节日,一般都是我们师徒三人在一起,虽然不像之前恩师的姑妈、张爷爷等亲属围坐一起那么热闹,但看得出恩师还是挺开心的。
随着同恩师的感情逐渐至深,我感受到恩师的孤寂不仅仅源于古琴的曲高和寡,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她的身世。我看到了这个时代所降临给她的困顿,进而看到恩师在面对这些困顿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这正好是她学养的最好体现,而这才是恩师对我最大的启迪和感动!
然而,恩师给我思想的启迪,远不止这些。
1992年的春天,我提出带她去南山春游,恩师高兴应允。这是我和恩师两个人第一次出去游玩,这时的交通,先要从解放碑坐公交车到望龙门,再坐轮渡到南岸,再上山。记得从解放碑坐车经过储奇门那段公路时,她指着路边山丘上一幢旧式洋房对我说,这就是他们家原来的房子,她从小就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当时只是在车上一瞥,有些印象,记得好像是一幢两层楼房,典型的民国时期那种青砖青瓦洋房,算得上民国时代重庆城里最富丽典雅的楼房了。可惜当时没有注意车行驶在具体哪段公路上,恩师去世后我还曾去这段路找过,也没有找到。她指着这幢洋房对我说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要知道平常我在恩师家里常能感受到姑妈和张爷爷提起昔时的那种荣耀感。难道恩师就没有在心里对比过现今狭小的陋室,但为何她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失意和抱怨呢?
也许“有大通必有大塞”指的就是这种情形,我开始感受到恩师那种抱持自性的本真。她的骨子里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我有时陪她出去,无论是游玩或者看病,她总是穿一袭黑色或者灰色的套装,利落得体,雅致脱俗。同时,我又能感受到时代带给给她的孤独和困顿。而现在,当我能够感受到她在这些孤独和困顿面前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即她对生活中一切迎面而来的境遇都真实去承接,她这种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更加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坚信恩师这种本真的人生态度,就像她那种大家闺秀的穿戴一样,很多应该源自她的文艺修为,于是我在接受她给我琴技上的身教言传之外,更多去思考艺术所包含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境界。
传统文化总是夹杂着好些流弊,容易给人造成故弄玄虚的道貌岸然,抑或追求形式的刻意解脱。在恩师身上,我没有看到她修炼了什么秘籍来应对生活,她在生活中遭遇一切,既不会单向地忍耐,也不会刻意去回避,而是自然而然地接受,自然而然地表露。每天她佝偻着严重弯曲的背到菜市场去买菜,回家洗衣做饭。生病了她独自去医院看病。琴破损了,她去找人修缮。
同样,我感受到她在用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古琴。她可以接受琴中那些超凡脱俗的修心,却没有刻意避世的死心。换言之,她既接受“琴者禁也”那些可以超越七情六欲的修炼,也保持着“琴者情也”那些生命应有的喜怒哀乐和责任担当。所以我看她弹琴没有丝毫的故弄玄虚和矫情造作。她当时其实并没有什么名家的光环,加上她朴素的平民生活状态,如果把这些放到现在,在那些对身边一大把真善美毫无知觉而在名家大腕面前魂飞魄舞的人们看来,实在是太不起眼。恩师的弹琴演奏更多的保留着蜀派的风格,可能在某些人看来会少了些清微淡远的雅致抑或心澄月明的意境,但她对琴的态度,就是她对生活的态度,她在生活中能够保持宠辱不惊的心境,她的情怀就是高远的,她用这种高远的情怀来演绎琴曲,她的琴韵又怎能不高远呢?
刚搬到文史馆,恩师的生活圈还算有些亮色。在搬家前不久,恩师前夫的亲属中有一位小姑娘叫小王,来与恩师住在一起,后来又随恩师一起到了文史馆。小王开始对古琴没感觉,因为同恩师天天在一起的缘故吧,渐渐也能弹上两三个小曲子。她曾以年轻人那种口吻对我说,其实学古琴一点都不难。不管怎么说,小王也算是恩师生前教过的最后一位学生了,也是我所见恩师收的第七位学生。
小宋也来这里看望过恩师,这是小宋最后一次来恩师家。当时便携式的VCD播放器几乎没有,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男友从日本带回来一个,她又买了古琴VCD碟,我们下班以后便一起去恩师家。恩师第一次听VCD,拿着播放器翻来翻去看,像个孩子。
因为就住在文史馆中,很多文史馆馆员和工作人员也常关心恩师。有位叫曹惠白的馆员,只要家里烧鱼炖鸡,都会给恩师捎来一碗。恩师特地把她的姓名告诉我,我便找到她当面致谢。另一位馆员江友樵,是知名书画家,住在文史馆旁边的宿舍楼,常来恩师这里坐坐。时间一长,小王也跟江老师学书画。我白天来恩师家,有时也会同江老师一起上三楼的书画室,看文史馆的老先生们创作书画。这些老先生都是当时重庆书画界的巨擘,观摩他们现场运笔,给我书画很大的裨益。我存有三枚心仪的印章,为馆员吴硕人所刊。他是知名篆刻家,他对古琴的崇敬出自一个他自拟的非常可爱的结论。他曾对我说,琴棋书画中棋的境界不如琴和书画,棋需要两人玩,易起争端,而琴和书画是一个人的空间,尤其是琴最能引人入心。故此他十分敬重恩师操琴,对我学琴赞许有加。
1994年夏天,恩师的眼病加重了。她的右眼近两年一直红肿发炎,去过多次医院效果甚微,慢慢病变成恶性肿瘤。一年前找到当时重庆的眼科名医开刀治疗,现在病情复发,病菌在扩散,右眼开始失明,整个眼眶肿得很大。恩师也知道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开始把自己所学的琴曲系统性地进行录音。恩师所用的录音机是我出差在广州买的一台国产燕舞牌双卡磁带录音机,当时这款国产名牌质量还算过得去。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经济条件好一些,给她买一台日产三洋录音机,那她留下的录音效果就会更好。她就用这台录音机和她珍爱的宋琴在晚上一首一首地开始录音了。她对学术是严谨的,每录一首曲,都要事先反复弹奏很多天才开始录音。录音时如果弹奏效果不满意,她又重新录,直到满意为止。这样,录音进展得很慢,从夏天一直接近年底才完成了十一首曲子,这时,她的眼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完全没有能力再进行下去。所以她平生最喜欢最擅长的曲目诸如《渔樵问答》、《高山》、《孔子读易》等都没有来得及录制,而《潇湘水云》仅录了一小部分,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她不无遗憾地翻录原始录音,一共翻录了大约十盒吧。她把这些磁带送给她认为应该送的人,比如文史馆馆长、文史馆办公室主任等人,把原始母带留给了我。
2016年《绝响》出版,收录恩师十一首琴曲,这些都来自那盘录音磁带。值得欣慰的是,磁带录音经过高科技处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有的背景杂音,音响效果得以提升。从这些录音中可以窥见恩师的琴学水准,比如她的《古寺钟声》,取音精准,自然流畅,很难想象这样娴熟的演奏水平竟然出自一位右眼失明、右脑巨痛、行将就木的人之手!
1995年初,她的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右眼早已失明,并肿大隆起来,整个右脸都因此变形,严重影响到大脑影响到睡眠。几个月来,她甚至不得不靠吃头痛粉来减轻痛苦。我每次整理房间,都能看到桌上堆放着成叠的头痛粉包装纸袋。
小王不知何故离开了,然后来了一位叶婆婆,这个称谓也是恩师让我这样叫的,至于是什么样的亲属关系我也没有弄清楚。叶婆婆明显是那种一生劳作的乡下人,她虽然目不识丁,但讲起杨家昔时的风光,也是赞不绝口。又过了些时候,叶婆婆也离开了。恩师寝室的斜对面是门卫室,门卫是个年轻人,平常和女朋友都住在门卫室,文史馆领导看到恩师这个状态,便请他的女朋友来照顾恩师。
恩师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很多次我要离开时,她总叮嘱我带些东西走。而我觉得这个时候拿东西走,好像真有些弥留之际的意味,所以每次都坚持不受。印象深的一次,恩师指着衣柜前面一只放在包装纸盒里的崭新的高压锅,非要我拿走,高压锅在当时也算是高档商品了。她都有些急了,我还是没有拿。我其实有过想要恩师影集的想法,最后还是没说出口,后来想起这事挺后悔的。恩师一共有两本影集,是那种照片贴在黑色底纸上的旧式影集,里面有很多恩师解放前的照片,还有恩师家人的照片。恩师孩童时期大约10岁左右时比较胖,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清瘦。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她孩童时偏胖的照片,有些不太相信是她,她露出她那特有的略显羞涩的表情点头称是。如果当初拿了这影集,再追问恩师一些事情,后来给恩师写资料,也会有更多内容了。
不过,就这样恩师还是让我拿走了两样东西,一是她的存款,有几千块,当时恩师家里凌乱,看到恩师将存单这里一张那里一张藏在书里或者衣柜里,我也不放心,便拿了为她保存。这些钱后来我通过文史馆交给她亲属,作为每年祭奠的经费了。还有就是《今虞》创刊,恩师给我这本书时没有商量的口吻,而是带着托付的口吻,要我把这本书好好保存。这本书极具史料价值,是查阜西、程午嘉送给恩师父亲的。当年恩师父亲或许也是这样传给恩师的吧,恩师便一直带在身边,少有示人,可以看出杨家世代对这本书的珍视。
这个时候,年轻的我处理事情总是不太灵活变通,有一件事让我抱憾终身。
二月的一天下午,她从床上坐起来,可能是剧烈的疼痛刚过去,精神稍好一些。她突然招呼我过去在床沿上坐下来,与我交谈,而且话多起来。这不是她的性格,她一向语言是很少的。
到了三月下旬,恩师近来右眼不时流出脓水和血,经常处于昏沉的状态。这一天她可能是夜里疼痛难忍,大脑神经也有些错乱,竟将屋里东西弄得七零八乱。据照看她的门卫女朋友说,恩师当夜紧紧地抱着宋琴,直呼有人要抢她的琴。后来我看到宋琴上沾有好多恩师眼里淌出的脓血,还有那本她总是放在桌上翻阅的琴谱,至今封面上仍有明显的血迹。
下午,文史馆为恩师联系好医院,就是位于观音桥的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文史馆的车在外面等着,恩师需要下床来走出房间。她身旁有那位门卫的女朋友,还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突然大家都发现她已经小便失禁,于是迟疑着,商议是否为她换衣服。有人说,如果换了衣服再走,路上可能还会小便失禁的,要不先到医院再说,反正医院挺近的。这时司机在屋外高声催促。看着众人小心翼翼翻动着恩师身上的衣服要搀她下床,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上前一把将恩师背在背上,径直就去到车里。坐在车上我才发现,我的双手、衣袖和背上满是恩师的尿液。后来常想起这个时刻,总弄不明是什么具体的意识能够在那一刻驱动自己一跃而起,也许这就是常说的素养使然吧。
恩师到了医院,仰面躺在病床上,闭着双眼叫我的名字。她要我留下来,说有要紧事。等其他人走了,结果她说的要紧事就是在她寝室的床头书柜里,琴谱中夹了一千六百元现金。其实恩师之前也把一些定期存折交给我让我保管,后来我到寝室里取出这些现金,令我有些吃惊的是,这些现金都是十元面值的,当时早有了百元大钞,可见这些钱是恩师平日里攒下的。后来我把这些钱交给了文史馆,用在恩师的后事上。
恩师在医院里几乎都是处于昏迷状态,靠输液输氧维持生命。几天以后,1995年3月30日凌晨将近两点,恩师走了。那时少有手机,我的中文传呼机29日晚将近十二点接到医院的信息。我匆匆赶到医院,这时恩师已经完全没有了知觉,唯有一丝呼吸尚存。我就在她病床边坐下来,盯着连接她呼吸的那个吊瓶中的气泡渐渐熄灭。
三十日下午文史馆开了一个会,由文史馆的卢主任主持,参会人员有文史馆两位工作人员,恩师前夫的两位亲属,连同我一共六七个人。卢主任拿出一份恩师的遗书,当着大家宣读起来。恩师的遗嘱写在一年半前,也就是1994年初,有文史馆书画家江友樵签字旁证,写好后交给文史馆馆长保存起来。遗嘱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恩师把那张终身相伴的宋琴连同所有的琴谱都传给我。恩师传琴于我,我此时方才明白,等卢主任念完遗嘱,我既吃惊,又感动。
第二天,我们便去到江北区的一个火化场。恩师的追悼会就在火化前举行,说是追悼会,其实到场的总共只有六个人,卢主任,文史馆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两位亲属,我和我夫人。虽然人少,卢主任还是挺严肃地主持了追悼会,他面对着我们五个人,代表文史馆高度评价了恩师的一生,赞扬恩师对重庆古琴艺术的贡献和成就。他大约说了三四分钟,说完后,问我要不要走到前面来也说一说。我对他摆摆手,他就没有再说了。整个追悼仪式就结束了。
我在此后的几年间,常常梦见恩师,大都梦见同她在一起弹琴。梦中她经常教我一些从未听过的优美曲子,醒来却忘记了。
2019年冬,方文伟叙于巴渝故里
资料整理协助:何红 史明江

 无障碍
无障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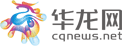
 手机阅读分享话题
手机阅读分享话题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